《论生命之短暂》的发散
照片
前几天我爸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考我是哪本书。我一看就知道是赛内加的《论生命之短暂》(De Brevitate Vitae),因为那本书是我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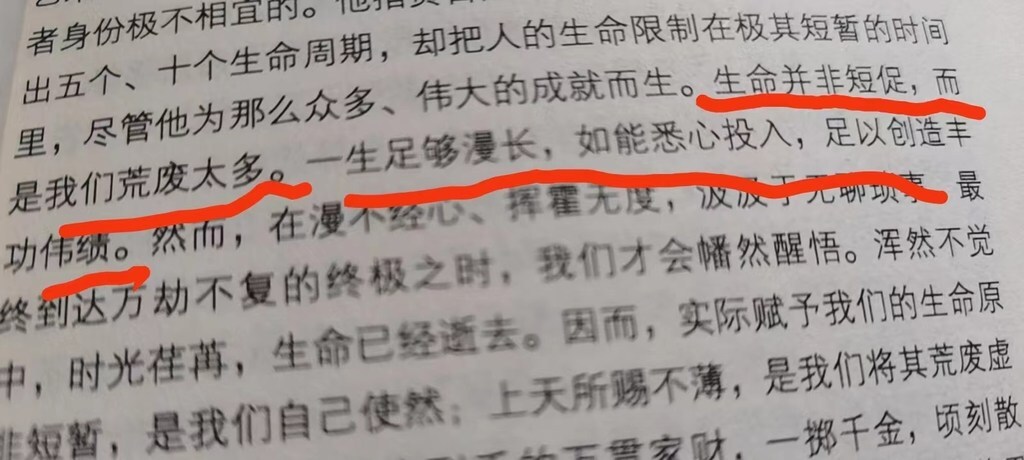
我买那本书并不是因为生活上碰到了什么坎坷而想要寻求斯多葛主义的慰藉。我买它的唯一原因是价格便宜,适合凑单。到手后开始阅读的原因也很简单:它又小又薄,可以很快看完。
然而等我翻到我爸拍照那一页,我才感受到手里这本小书不只是用来凑单的附赠品。“生命并非短促,而是我们荒废太多。”听起来当然不如“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振聋发聩。但这句话却能刺痛每一颗对时间流逝抱有愧疚的心——换句话说,是刺痛所有人的心,因为没有人不对逝去的时光感到遗憾。所有人都会有悔不当初的感叹。而一旦有一丝这样的想法,就会被赛内加的这篇文章击倒。虽然赛内加在口若悬河,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后悔。
所以,这位帝王之师、智者元首有什么解决方法?答案是:停止工作,投身哲学。
有一本忘记名字但很有名的科普书声称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就是物理学家。如果现在的科学就相当于古时候的哲学,那我可以说——额,好像还不能说我做到了投身哲学。因为我在学校学习、在公司实践的似乎相比科学而言更贴近技术。关于科学的定义,还是下回再说吧;关于技术与生命,倒让我想起一句古话:
Ὁ βίος βραχύς, ἡ δὲ τέχνη μακρή
我不懂希腊文,用它作小标题只因它是原文。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是在《神枪少女》的中段:研究员用“人生苦短,技术永存”向读者预告主角团要有人退场了。

后两格给我很大触动,其原因当然包含对主角团的悲伤,但更多的是对技术“永存”的敬畏。不过一年半后的现在再看这句话,我已经感不到技术会永存了——可能因为工作上十多年的屎山代码要重写了。事实上,这句译文并不贴切。希波克拉底的原文还有“机会流逝,实验危险,判断困难”。按照上下文理解,前两句应该翻译成“生命短暂,(学习)技术漫长”——非要贴近汉语的话,也得是“人生苦短,学海无涯”。
后来再次看到这句话,是在Bash、Readline的维护者Chet Ramey的个人主页上:他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乔叟的“The lyf so short, the craft so long to lerne”。联想到这位Chet维护了Bash近三十年,我又感觉希波克拉底那句话意在歌颂尝试用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技术搏斗之人的精神。
先放下生命很短这件事,单说希腊语的技术(τέχνη)——因为我早想说说高德纳那排版软件TeX的读音问题了。高德纳声称TeX之名来自英文Technology的语源τεχνολογία(技术τέχνη+学习λογία),因此TeX也该按照τεχ的读音念(国际音标:/tex/)。国内有人用“泰赫”来强调/tex/,但英国还是念tech(/tek/)的人比较多。我问过把loch的ch念成/x/,却把TeX的X念成/k/的老师为什么不按希腊语的发音读TeX。那位老师说因为他没正经学过希腊语,所以按英文的读法读。这很有道理,如果一个人不会俄语却偏要把AK-47念成“阿卡四十七”,那确实有够别扭。
关于这段话另外一点想说的是希腊语、拉丁语和英语里的技术(τέχνη、ars、art)都同时有艺术之意。那技术和艺术的分界在哪呢?个人认为,看完能为自己所用的是技术,只能称赞的是艺术。比如高德纳那套《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要是你看完能融会贯通,那就是《计算机编程技术》;若是看完只能说牛逼,那就是《计算机编程艺术》。当然,因为“Vīta brevis, ars longa”,所以不看那套书也完全没问题——这也是我为什么不看的原因。
哲学不是卡牌游戏
我有次和两个同学在海边吃炸鱼薯条时聊到了塞内加。当我说出塞内加是罗马哲学家时,其中一位谢林粉丝立刻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屑。问他为啥,他说:“罗马哪有什么哲学?全都是希腊玩剩下的。谢林说的!”后来我和其中另一个同学聊到哲学时又被批评“你还处在没有走过康德之桥的庸俗哲学呢”。
他们好像把哲学当成了卡牌游戏——当我的德国人卡牌发动攻击时,将你手上罗马人、英国人、美国人卡牌全部送入墓地!这,让我十分不解。因为在我眼里学习哲学是为了辅助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当作获取胜利的卡牌。
哲学和生活不冲突
既然提到了哲学与生活,就不能不声明这两个元素之间没有冲突。我爸虽然不阻止我看哲学书,但总是在聊到哲学时说哲学是他那个年纪才应该学习的。多巧啊,我近几年对哲学产生兴趣的根源就在于中学时在他书架上看到那本《科学哲学》。他告诉我那是他研究生时期老师编的教材,他还说那位老师很老了,但上课时仍然思维敏捷眼睛放光。后来当我在选修课列表里看到《科学哲学》这门课时,我立刻想起了那本书。可能有些重走长征路的想法吧,我选了那门课。
那门课的老师和同学都很好,但上完课我只感到不满足,然后我买了《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我其实很早就接触过哲学,就算在大学期间,《科学哲学》也不是我选的第一个哲学相关课程。但之前接触时的叙述方式都是从“世界由水/火/气构成”的哲学史开始——我对历史完全没兴趣。《大问题》以话题介绍各个哲学观点,这对我来说就像猪油一般美味。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Jeff Erickson在其《Algorithms》前言里的一句话:
Finding the author that most effectively gets their intuition into your head takes some effort, but that effort pays off handsomely in the long run.
总之,《大问题》就是最对我胃口的那本哲学教科书。我看得很慢,没看完就出国了。然后老爸也开始阅读它,边看边在微信群里告诫我少搞哲学专心生活。看完《大问题》后他赞叹不已,接着开始看引出这篇博客的那本书。
虽然我和他解释过了年轻时看哲学书不影响生活,但想到可能还有人抱有“过早思考这些终极问题,会影响到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想法,所以我再重申一下:
- 想不出答案远比没想过问题要好;
- 可以同时有几个答案,毕竟现实生活不是答题;
- 临时的答案也可以指导生活;
- 过晚思考更容易导致“浑然不觉中,时光荏苒,生命已逝去”的结局。
当然,在哲学不应该挡住生活的道这一点上我和老爸站在同一战线:要是吃顿大的都要犹豫,还是先努力工作吧。按照《论生命之短暂》的说法,塞内加是否定工作的。不过他那么说是有原因的:
塞内加是道德家还是骗子?

曾被认为是塞内加的假塞内加像。符合人们对斯多葛派哲学家的幻想。Digital image courtesy of Getty’s Open Content Program.

真正的塞内加像。一看就是回扣吃多了。Sergey Sosnovskiy,CC BY-SA 4.0
塞内加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完全是两码事。《哲人与权臣:尼禄宫廷里的塞内加》说:
塞内加对言语和论据的巧妙操控使得他可以同时做到两件事情:阐述他的斯多葛理想,同时改善自己的政治形象。
大约成文于公元40年的《致玛西娅的告慰书》(Consolation to Marcia,又译作《马尔齐亚的慰藉》)所采取的写作形式,是一封写给一位为死去的儿子悲伤的母亲的信,但塞内加写这封信的本意就是想要将其公布于众。塞内加一生都在玩这种修辞把戏,让他的读者们能够旁听这场看似私密的交流。
虽然并没有什么证据去证明这个理论(塞内加出于自身利益去安慰玛西娅),但是这符合塞内加大部分作品展现出的机会主义模式。他对文字的掌控是如此娴熟,他的修辞技巧是如此精妙,以至于他很容易在助人的同时自助。现代读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任何一部给定的作品当中,判断哪一种动机是最重要的。或许,塞内加自己常常也不清楚。
那么他写作《论生命之短暂》的动机是什么?
公元55年,由于阿格里皮娜的设计,塞内加在宫廷中遭遇挫败,此时阿格里皮娜已经与塞内加势如水火。为了炫耀自己的胜利,阿格里皮娜将自己的一个党羽——法伊尼乌斯・路福斯(Faenius Rufus)任命为监粮长官,这就意味着塞内加的岳父保里努斯必须下台。这种贬职令塞内加和保里努斯都倍感难堪,除非这种行为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自愿而高尚的事物:一种哲学上的避退。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塞内加写作《论生命的短暂》的目的,这篇论述是写给保里努斯的,以敦促他采取这种避退。
这部论述的最后一部分是一个颇为巧妙的顾全颜面的设置,是现如今表示希望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的这种陈词滥调的更为崇高的版本。
这就是为什么塞内加“否定工作”:因为那封信就是为了给失去工作的岳父找台阶。
塞内加的信件不止有多重意图,还相互矛盾。我买的那本《论生命之短暂》是个信件集,收录了塞内加被克劳狄乌斯流放到科西嘉岛上后给母亲写的《致赫尔维亚的告慰书》。那封信中他表示自己喜欢这个荒凉的流放地,金钱家产从来不是自己关心的。然而第二封信就使劲拍克劳狄乌斯的马屁,以期回到罗马:
在塞内加流放时写的第二封公开信件中——这封信可能是在第一封公开信完成的一两年后写成的——他委婉而迫切地表示,他非常渴望克劳狄乌斯皇帝将他召回。
塞内加在他第一封从科西嘉岛送出的信中所描述的闪耀着光辉的灵魂阿卡迪亚(Arcadia),在第二封信中已经化为乌有。他所生活的岛屿已不再是大自然的有益犒赏,而变成了一块条件严苛的贫瘠岩石。塞内加并没有直抒胸臆,而是表示,一位文明之士绝不能在这样的地方腐烂。塞内加从奥维德那里借鉴了一些伎俩,他为自己的行事鲁莽而道歉,并且声称,仅仅是听到那些野蛮人发言时表现出的粗鲁喧哗,就足以让他那聆听拉丁语的耳朵备受损害。
他的《致波里比乌斯的告慰书》(Consdation to Polybius)被几乎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虽然塞内加本人或许并不希望如此。
把塞内加作为富豪却讴歌赤贫、协助尼禄杀弟弑母的嫌疑先按下不表,他的作品到底值不值得读?
我的答案是值得:他是真正的道德家还是骗子对我来说并无所谓、公开信的真正意图也无所谓。只要我有所收获,即可——鱼有刺,就不吃鱼了?把不好的东西剃掉不就得了。
《哲人与权臣》里也有类似的评判:
最后,塞内加是人,他有人性的污点和缺陷,这是人之常情。正如他在数次辩解中的某一次所暗示的那样,他并非完人,而是胜于庸劣。这对于许多读者而言也就足够了。
说实话,当提到“讴歌贫穷的富豪”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一点也不喜欢钱”的马云。现在他在互联网上被斗倒斗臭、全盘否定了,但我仍然认为他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了,“Vīta brevis, ars longa”,我是懒得在他身上挑优点。塞内加的作品毕竟是经过小两千年了还在印刷;马云也许到下个世纪就没人提了。
其实罗翔也很像塞内加:都言行不一,都善于向公众讲述高尚的品德。我对罗翔的看法也和对塞内加的看法一致:吸收好的,剔除坏的。所以有时还是会点开他的视频,看看能不能淘点金子出来。
《哲人与权臣》里引用了昆体良的话来总结塞内加的文学风格以及他令人疑惑的品质。我觉得这几段话也能用在马云、罗翔身上:
他的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赞许的地方,甚至也有很多值得我们钦佩的地方。
只要在做出选择时谨慎一点就行了。
要是他当初也是这么谨慎小心就好了。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
对于自杀的狂热赞颂是塞内加思想中的第二个重要标志。
后世认为塞内加的名字取得恰如其分,因为“塞内加”这个名字可能源于拉丁短语“自我了断”(se necare)。
我说过我很关心作品的结局,其实我也同样关注作者的结局。如果在谈论塞内加的闹剧时不讲述他的结局,就像聊家常菜时不说小炒黑木耳。
在收到推翻尼禄的邀请后,塞内加既没加入也没拒绝,只是回复了模棱两可的“自己的福祉将取决于披索(密谋者准备推选的下一任元首)的安危”。
事情败露后,塞内加期待尼禄判他流放,不过尼禄并不想让他活下去,所以塞内加只得自杀。这位赞颂自杀的哲学家先是划开自己的血管——失血身亡太慢,他甚至向书记员口述了最后一部作品(狄奥说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反尼禄作品,但现在没人知道是哪一部)——然后塞内加又饮下了(为模仿苏格拉底而准备的)毒芹汁,仍然没死。最后他没办法,走进了浴池里,死于蒸汽窒息——死前还不忘模仿苏格拉底向神灵致敬。
谣言说一些禁卫军打算等披索上位后杀掉披索,拥立塞内加。也许在某个平行宇宙中塞内加成为了元首,那哲学王的名号就要归于塞内加,而不是奥勒留了。
本小节的标题和加缪没关系,我只是因为自杀而想起了这句话而已。塞内加不可能纠结生命是否值得过,他曾在《梯厄斯忒斯》里表达过自己的心声:
对生命的贪婪是他拒绝赴死,和那垂死的世界一起消亡的原因。
所以生命到底短不短?
短,如果需要精打细算才能显得长的话,那就是短。
洗碗时突然想起《格列佛游记》里描述了一种长生的人。虽然长生,但没有不老。他们衰老到无法阅读,衰老到无法学习,最后连和他人交流也做不到了:
The language of this country being always upon the flux, the Struldbrugs of one age do not understand those of another; neither are they able, after two hundred years, to hold any conversation (farther than by a few general words) with their neighbours the mortals; and thus they lie under the disadvantage of living like foreigners in their own country.
这么一想,不只是生命很短,而且是青壮年时期很短。决定了!明天开始给自己打叶绿素。
记录自己的生活
记录生活并不一定能让生活变得好过,我写日记只是因为我喜欢笔尖摩擦纸的感觉。但如果以生活也需要练习,而日记相当于错题本的角度去想的话,那记录生活就有益处了。
其实记录生活的方式不止有写日记、发朋友圈。把浏览器的历史记录、手环的心跳记录、地图和照片的位置记录、银行的消费记录等等在暗处不断累积的记录导出来,也是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要导出来才算,不导出来的话只是别人记录你)。
理论上来说,收集的记录越充分,就越了解你自己。在日后做判断时,也就有更贴近自己的标准。网上有个神人在四年间记录了380,000项关于自身的数据,生成了42张眼花缭乱的图表。我十分佩服这位,然而他在网站上特意突出了这句话:
The main conclusion is that it is not worth building your own solution, and investing this much time.
我其实也曾痴迷于记录自己的时间——用一款叫toggl的软件。后来发现我只记录,不分析,所以很少用了。对我来说,用笔划拉纸的方法不仅够用,而且令人开心。博客的话,其实是能贴图片的日记。
 复制以下链接,并粘贴到你的Mastodon、Misskey或GoToSocial等应用的搜索栏中,即可搜到对应本文的嘟文。对嘟文进行的点赞、转发、评论,都会出现在本文底部。快去试试吧!
复制以下链接,并粘贴到你的Mastodon、Misskey或GoToSocial等应用的搜索栏中,即可搜到对应本文的嘟文。对嘟文进行的点赞、转发、评论,都会出现在本文底部。快去试试吧!